本文源自:互联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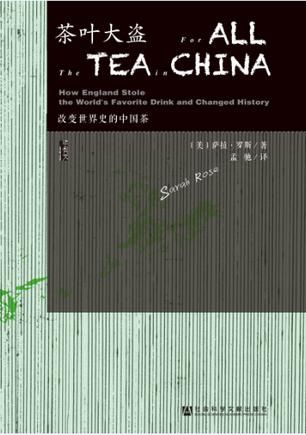 《茶叶大盗》,(美)萨拉·罗斯著,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茶叶大盗》,(美)萨拉·罗斯著,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茶叶和丝绸堪称清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尤其茶叶,更是19世纪中叶中国维持对外贸易平衡的重要砝码。但从1880年起,以印度为原产地的英国茶叶异军突起,英国至此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茶叶贸易国。中国茶叶竞争力的丧失,其关键原因在于一个叫罗伯特·福钧的苏格兰人的跨国偷盗行为。该行为被为其写传的美国历史学家萨拉·罗斯称为“近代以来最大商业秘密盗窃案”。
罗斯在《茶叶大盗》中记录了福钧在中国自1848~1851年间的间谍行动。福钧乔装打扮后在中国仆人的帮助下走遍上海、浙江、福建武夷山等地,采集高质量茶种和招募专业茶工,运往印度喜马拉雅山种植园。罗斯摘录的福钧日记、信件和回忆录也“直播”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通商口岸与内地农村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种种面貌。喜爱故事的读者大概还能读出“植物猎人大战腐朽帝国”这样的怪奇玩意,而对我来说,福钧此行的动机及其意义才是最值得咂摸的。
正如游戏角色与boss最终对决前总要通过打怪升级来聚敛宝物和经验值,福钧也备齐了中国行的所有利器和法宝。尽管罗斯刻意将其描绘为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但她还是非常仔细地为我们罗列了福钧这一身光闪熠熠的行头。我稍微梳理了一下,约有这样三大件吧。
一是大英帝国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目标。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和英国各自垄断了彼此的茶叶和鸦片贸易。英国把向中国出售鸦片赚取的利润用来购买茶叶,并对茶叶征税,而茶税已占英国总税收的10%,成为英国用以进行国内基础建设和海外殖民扩张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担心中国宣布鸦片贸易合法化进而在本国种植鸦片(这一担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成为现实),会危及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并造成英国单方面依赖中国茶叶进口的糟糕局面。因此,在印度大规模种植茶树,便被提上了英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二是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和财政危机。迄至1834年,持有英国政府特许状的东印度公司一直垄断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但随着英国国内政治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兴起,东印度公司的特权地位摇摇欲坠。1813年,英国议会终结了公司在对印度贸易上的垄断权,1834年又取消了它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在此背景下,公司开始尝试在印度种植茶树,来确保自己在自由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但它发现印度本土的阿萨姆茶叶和喜马拉雅山茶品质不佳,从广州偷运进口的中国茶叶也并非上等茶种,而在茶叶的种植、栽培和制作上,更是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对优质茶种和人才的储备需求,成为公司存续的生命线。
三是英国的城市化运动与科学技术上的突破。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大量农民从乡村迁入城市,土地被有钱的乡绅圈了起来。乡绅们建起草坪和花园,满世界寻找奇花异草点缀其中,客观上推动了植物全球贸易的井喷(并造成植物大入侵的灾难性后果),而英国的殖民政策也正好呼应这一潮流。19世纪最伟大的“植物猎人”和园艺家福钧此前只是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贫寒农家子弟,这一潮流则让他入选皇家园林协会,与当时最好的植物学家切磋交流。而植物贸易全球化对植物的运输和保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沃德箱”这一划时代的发明应运而生,它后来经由福钧的改造而在偷渡国境的旅途中大显身手。
如此,福钧的冒险设备全部配齐:大英帝国的全球政策为其撑腰壮胆、保驾护航,东印度公司提供生活、工作与科研经费,皇家园林协会和“沃德箱”则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持。国家、财团和顶级科学机构同时为某个个人提供最高级别的资助,这是大航海、大冒险时代才会发生的事,于今可能已经无法想象了。
而福钧千辛万苦偷盗的成果终于在喜马拉雅山种植园中大放异彩。罗斯从地缘政治经济、英国人生活与饮食结构等方面,探讨了茶叶本土化种植对英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
经由印度的成功经验,英国把茶叶作为殖民扩张的工具,在缅甸、锡兰、东非及其他合适地区遍植茶树,建立地方产业经济,并加速对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形成由英国主导的全球商贸网络体系。
在运输上,人们对新茶的热衷使得船舶航速实现了突破性的飞跃。人们淘汰了拿破仑战争后继续服役的笨重商船,而改用小巧实用的快船。自由竞争更是加速了快船的更新换代,泰晤士河上的运茶比赛成为伦敦市民一年一度争相目睹的大型体育赛事。
在生活上,自由竞争引起茶叶价格大幅下跌,原来只是贵胄之家才能享用的饮品,普通民众也能消费得起。同时,自由竞争也使商家特别爱惜自己的品牌,遏制了以次充好或往茶叶中添加危险化学品的动机。而茶叶的普及也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英国人往茶里添加糖和牛奶带动了这两样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减少了酿酒行业对小麦生产的依赖,确保了迅速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等等。
不过,这些只是英国人的好处,中国人不仅不沾边,反而深受其害。我发现,尽管罗斯认为福钧的偷盗行为本质上属对个人、企业和国家生存都极重要的“知识产权”的侵犯,但她仍将其视作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那样造福整个人类的英雄壮举,仿佛中国人并不属于“人类”。她描述福钧潜入中国茶叶工厂偷盗技术、挖人墙脚、揭人之短的口吻,好像007大战某个邪恶组织那样以正义自诩。特别是,她如此描述福钧的中国行成果之一(用以茶叶染色的化学品)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公之于众的意义,“福钧揭示了那些中国人在无意之中犯下的罪行。这将为英国自行种植、加工茶叶提供无可辩驳的依据”。
而事实上,同时代的英国茶商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此事为英国茶叶种植者和作家罗伊·莫克塞姆在其《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披露过,莫克塞姆还呈现了印度的英国茶叶经营者盘剥和迫害被雇来或骗来的印度和中国劳工,其残酷血腥令人触目惊心。在他笔下,茶香与血泪是分不开的。这些都为罗斯一笔带过,或经浪漫化处理了。不得不说,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偏颇写法是让人稍觉遗憾的。



